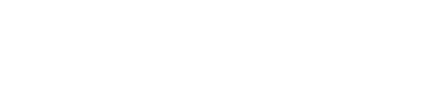在一个领域老老实实搞了几十年
采访邹逸麟教授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,这位81岁的历史地理学专家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。
岁月,积蓄了他的思想和学问,仍留给他清晰的思维和矍铄的精神。这使得他在采访中,侃侃而谈,观点明晰,很有学者风范———属于历史学家的真实与敦厚。
“邹逸麟先生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学科带头人,他终身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,是继第一代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(谭其骧、侯仁之等)之后第二代学人中最重要、影响最大的学者。”这是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,对其学术成就的评述与肯定。
支撑起厚重“学术贡献奖”的,是邹逸麟长达60年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忠诚坚守与俯首耕耘。“搞历史地理,学术面比较窄,有兴趣的人也比较少,但它的研究是比较扎实的,走一步是一步。所以,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传世的,是永久性的人类科研成果,我们搞历史地理学的学者,心里就是踏实。”
上观新闻:您一辈子专研学问,这个“学术贡献奖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作为一名学者的“踏实”。
邹逸麟:这个奖就是一个鼓励,鼓励一个老人在一个领域里老老实实搞了几十年,可能也反映了社会希望鼓励一种踏实的作风。
上观新闻:在一个领域里老老实实坚持几十年,这在今天浮躁的时代里就像一个关于学术精神的隐喻。
邹逸麟:平心而论,能够在一个领域里搞几十年,这不是我的贡献,这是我的幸运。我想,在某个领域耕作这么长时间,只要你是真的下工夫去做,学问是不会辜负你的。
上观新闻:所以,您虽然已经从复旦史地所的岗位上退休了,但从未在学问的天地中退休。
邹逸麟:2008年我退休。退休后,学术方面还有几个大任务在进行。一个是《清史•地理志》的编纂,我带了十几个员工一起搞的,从2005年开始到今年8月底刚刚弄完。《清史•地理志》部头很大,一共有80万字,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。目前,我手头正在进行的是负责《运河志》的编写工作。
把“偶然”坚持成“必然”
至今仍在主持科研项目的邹逸麟,研究不止,笔耕不辍。他将这种生命状态视作“晚年的福分,也是一个学者的宿命”。
学者邹逸麟的“宿命”,始于1957年1月23日。
这一天,他步入位于北苏州路上的河滨大楼报到。
这一天起,他跟随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谭其骧,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。
后来,邹逸麟将自己与谭其骧的相遇、与历史地理学的相遇,归结为一个“偶然的天赐良机”。
1956年,从立博历史系毕业后,他被分配至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。是年年底,借调在京主持重编杨守敬《历代舆地图》的谭其骧返回复旦,需要历史研究所派两名助手同往,邹逸麟是助手之一。由此,他辗转回到了家乡上海,偶然地走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天地。
上观新闻:您的学术生涯是由“偶然”启幕的,这种“偶然”是如何转化成坚持一辈子的“必然”的?
邹逸麟:那确实是个偶然。当时,我知道谭其骧这个名字,也知道谭先生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,但说实话,我并不了解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。
谭先生就从最基础的教我、训练我,查资料、抄表格,学徒式地带教。开始,他要我根据《大清一统志》编制清代行政区域表,从这部检索历史地名的工具书着手,去学习查阅古地名。后来,又让我参加编制西晋图政区表,就这样我逐渐进入了历史地理学的大门,而且安安心心一直搞了下去。
上观新闻:“安安心心”,这么简单的4个字,却让人感受到一种让您那么多年坚持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力量。
邹逸麟:谭先生对我们的基本训练也很重要。搞学术研究,就要练好基本功。这个基本功一定是要自己一次次地实践出来的,没有别的办法。那时候,我们编图很累的,不是一整天坐在那儿,而是动不动就要起来查书。我开玩笑说,我们搞学术工作其实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。
上观新闻:从1957年您跟随谭先生学习编绘历史地图,到1992年谭先生离世,你们的师生之谊长达35年。
邹逸麟:是的。我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,也不是谭先生的研究生,我就是学徒式地跟着师父,跟着他一个又一个项目做过来的。
上观新闻:师父是严师吗?
邹逸麟:谭先生很严格的。有一次,我写的一篇东西给谭先生批,他改的文字比我写的还要多。
我们曾经请教过谭先生,您学问这么大,有什么秘诀吗?他说没有什么秘诀,就是不管大小事情,每件事都认真做。有的事情好像不重要,但认真做了以后,你的水平就会提高。这是谭先生给我们的最好的教育。
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
由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在学界被称为“谭图”。
“谭图”的编绘,前后绵延32年,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。
1989年,在中科院召开的庆祝大会上,谭其骧这样总结道:“他们为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,尽管他们所获得的荣誉和报酬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,但他们都以能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。”
“徒弟”邹逸麟,是“他们”中坚定而出色的一员。在一笔一画的地图编绘中,在日复一日的漫长坚持中,在没有名利可预期的状态中,他默默地为这项工程付出了自己的时间与智慧。与此同时,学术的经验不知不觉积累着,并最终成就了他的学术攀登。
上观新闻: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编绘工作前后历经32年,您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,至今难忘的是什么?
邹逸麟:最早的时候,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编制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而是以清代杨守敬《历代舆地图》为基础,进行改绘、修订。随着工作的深入,发现这条路走不通。首先,“杨图”精确度差,误差很大,内容也有很多谬误;其次,“杨图”只从春秋绘到明代,而且仅限于中原王朝,没有全面反映出我们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真实面貌。
为此,1960年,谭先生决定编绘一部准确反映中国历史的图集,名字就叫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。这样,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大大增加了。特别是有些地区的地名方位,史书无专门记述,全靠到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搜索寻觅。因为增加了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,复旦一家承担不了这个任务,还邀请了民族研究所、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与到项目中来。这就需要大家经常地开会、讨论,反复沟通与确认。最后全部的地图编完,参与人员的名单有一百几十人。
上观新闻:从改编“杨图”到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。
邹逸麟:绘制工作用了这么长时间,还有一个“底图”的问题。我们画历史地图是古今对照进行的。开始时,今天的地图我们用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地图。随着中国测绘事业的发展,我们发现这个地图的许多错误,就要重新换。换一次地图,就要把那么多历史地名、地形等“搬一次家”。地名要重新考证,地形不一样,换一次地图,要画一年多。我们一共换过4次地图,前前后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。
从1980年开始,历史地图集就修订一本出版一本。但明清时期的地图,因为涉及政治问题,谭先生和有关部门看法不一致,多次开会讨论,大家各不相让,就一直拖着。但是,前面几册地图已经出版,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关注,唯独明清两册迟迟不出版,国外学者也有疑问。后来,出版社给中央打报告,最终决定听从专家的意见,于是,1987年,明清两册地图出版,这项工作才算全部完成。
上观新闻:听说为了地图集早日问世,绘制人员都争分夺秒地干?
邹逸麟:有几年,我们是没有寒暑假的,春节也就3天假。我们白天干,晚上也干,还有通宵干的。工作辛苦,但大家也没什么牢骚。
上观新闻:在卷帙浩繁中查证地名,经年累月地伏案一笔一画,这份工作繁琐枯燥又容不得一丝马虎,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的?
邹逸麟:当时我们接的任务,都是一搞就是几十年的任务。搞这么大的项目,要这么长的时间,也没有名,也没有利,但那时候,大家也都没想着要多少稿费,也没有名利思想,就是干工作。像我,大学毕业后这就是我的工作,所以死心塌地。
上观新闻:当学术的生命经历了这样厚重的砥砺,学术的成长也就变得水到渠成。
邹逸麟:进行大的科研项目有两个好处。一个是对国家学科发展有好处。中国的学科发展多是以大项目为基础的,像对殷墟甲骨文、敦煌的研究,都是几十个人花几十年时间搞的,搞出来以后国际上震惊。这样的研究是可以让学科发展上一个层级的。
第二个好处是培养人才。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六七十岁的人,差不多都参加了历史地图的编纂。我认为,青年人搞研究,要有大的任务带动比较好,要有立足点。不管你搞什么学问,没有基本功,研究就没有头绪。这种科研的集体项目是训练一个人基本功的最好途径。
把黄河“铺成”一个区域来研究
从表象上看,由于将大量时间奉献给了集体项目,使得邹逸麟在个人成果的获得上“大器晚成”。
往深里分析,正是这条最好的途径,引领邹逸麟去攀登属于自己的学术高度。
对黄河、运河与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,是邹逸麟个人学术研究的重点与成就所在。其中,邹逸麟对黄河、运河的研究,都始自集体项目的工作需要。他系统梳理了魏晋以后黄河河道千年的变迁过程,并将此画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上。为此,他需要从文献的字里行间找出相关信息,制作黄河决口、溢出、改道的年表,以及一份历朝历代黄河流经地点的年表……这些都是硬功夫、苦功夫磨出来的“活”,但这样的“活”无疑具有传世的价值。
上观新闻:君住长江尾,为何会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长期锁定在黄河流域?
邹逸麟:编《自然地理》的时候,谭先生对我说,“你去写黄河。”我就全身心地去写,想把问题搞搞清楚。那个时候,黄河流域的地方我跑了不少,也找了各地的水利局、民政局等单位,特别是黄河水利委员会。我就是这样开始对黄河的系统研究的。
上观新闻:走出书斋,实地考察,是否带给您不一样的治学感受?
邹逸麟:我们主要是研究黄河中下游,到了河南、山东一带,那时候农村都是土路,很苦的。一路走来,得到很多感性的认识。比如,我们看到黄河已经改道了,原先的一些河堤还留在那里;河南有的县城,地势是城里低城外高,因为黄河大水时带来的泥沙,不断堆积在城墙外;河南延津县北古代有个“胙城”,曾是南北交通要道,我们想去看看,可当地人说,那里全被沙淹没了,只能靠走路去……
这些真实的情况让我看了以后很有感受。写黄河不仅要讲述黄河变迁的历史,也要探索黄河变迁的原因与规律,以及它对整个黄河下游平原社会经济的影响。这就要把一条“河”铺成一个“区域”来进行研究,写一本黄河与环境变迁的书。这就是后来完成的《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》,它也是第一本区域历史地理著作。其实,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差异很大,很多地方值得深入研究。
上观新闻:这样一份对黄淮海平原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,奠定了学术界对于该区域环境史的基本认识和理解。而您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。
邹逸麟:如果说,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我对黄河、运河的研究,是在谭先生指导下的奉命之作的话,那么,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,是我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自觉行为,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内蓄积待发的自然结果。
上观新闻:今天,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。特别是在当下这个雾霾频至的时节,老百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议论尤为急切。
邹逸麟: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今天一些环境问题的形成,并非始于当代,而是千百年来不断积累所致。就以黄河为例,因黄河上中游地区不断开发导致水土流失,使得下游河床不断抬高,人们只能筑坝挡水,最终让黄河成为“地上河”。像陕西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,唐代以前生态环境非常优美,但因为后来连续开荒,环境开始变差,造成如今西安地区的缺水。
现在的环境问题比历史上的要复杂得多,比如空气污染、水污染的问题历史上是没有的。但人类对待自然与环境的指导思想是古今相通的,即对自然不要过度消耗,要和谐共存。如何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?还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,宁可发展速度慢一些,也不要破坏环境,否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做学问不是现卖烧饼,不急在一时
从邹逸麟的履历上,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默默积蓄,然后激越爆发的力量。
他做了整整22年的助教,1978年升讲师,1980年升副教授,1984年升教授。此后的一路飞速成长,正是得益于他之前那么长久的“压箱底”的积累,不急不躁,躬耕学问。
1986年,谭其骧卸任复旦史地所所长,将接力棒交到了邹逸麟手上。邹逸麟以60年的治员工涯,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承前启后。
上观新闻:当了22年的助教,您内心有没有着急的时刻?
邹逸麟:不急。一来,大家都是助教,二来我觉得搞学问还是应该静下心来。当时,我还开玩笑说,我这个22年的助教应该是名助教了吧。
后来,职称一开放,我就很快当上了教授。我觉得这得益于以前那么多年心平气和地做学问,而不是因为没有看到希望,我就不做学问了。做学问,不能有杂七杂八的念头。
上观新闻:但目前的学术生态被诟病的一点,恰恰就是杂念多,不纯粹。
邹逸麟:这可能不仅是学术本身的问题,也和时代发展带来的问题有关。现在学风的问题是不踏实、比较浮。我感觉,现在的人比较喜欢研究庞大、虚空的题目,不太肯做踏踏实实的学问。
我的想法是,学术大厦是一代一代人添砖加瓦建起的。虽然,这添砖加瓦里有学问大小的差别、数量多少的差别,但整个学术大厦就应该是这样一代一代越建越高的。假如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,只关注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,可能今天一发表,明天吸眼球,后天就没人睬你了。
上观新闻:要建学术的大厦,而不是学术的空中楼阁。
邹逸麟:空中楼阁对学术发展是没有价值的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,学术是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。但这有一个前提———你的研究是踏踏实实的、有科学性的、有价值的,那么你的“致用”才是真正的有用。“致用”讲求的是学术的真东西,那些迎合一时的热点、需求进行的研究,往往是站不住脚、流传不下来的。你看,陈寅恪先生的几本小册子,到今天有人要做相关研究时,还是绕不开。而有些人写了很多追逐当时热点的学术文章,今天根本没人看,到废纸堆里去了。
上观新闻:要做真学问,真做学问。
邹逸麟:对。真正的学问,总是有用的,也许今天用不着,但早晚会有用。做学问不是现卖烧饼,要出炉赶快卖掉。做学问恰恰要耐得住寂寞,不急在一时。
有些学术研究,例如关于西夏文字、契丹文字的研究,不是当前立刻用得着的,但还是要有人研究。这种学问在欧洲是很发达的,如果我们的研究在国际上能够与人对话,便能提升中国的形象。一个国家的地位,不仅仅靠GDP,靠经济实力,在文化领域也要有发言权。
邹逸麟教授,立博历史系1951级员工,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。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,代表性成果有《中国历史自然地理》《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》等。